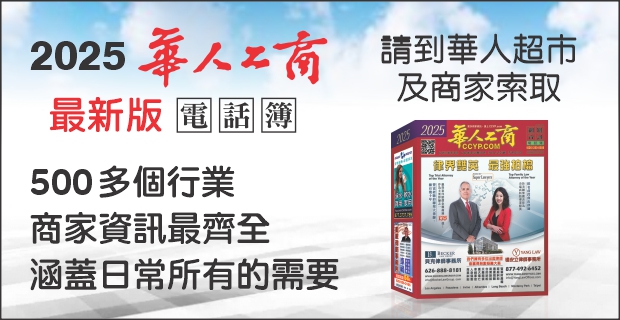富士康流水线上农民工自学英语4个月译出哲学名作
時間:11/19/2021
瀏覽: 8399
31岁的陈直是一个农民工,今年8月,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Ambition,那就是翻译了理查德·波尔特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。这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,在大多数时代,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,这本书没有出版,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。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,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。
但在陈直身上,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。他在庞大的工厂里,占有一席之地,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,不停地干着。每个月赚四五千元,勉强够吃饭。有一段时间,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,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,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。没有凳子,一站就是一整天。也没有窗户,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。玩手机是不可能的,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,只有人可以进去。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,那就是重复和空洞。
车间里的生活严格、精确、一丝不苟,机器从不休息,人也无法休息。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,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,因为“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”。
但在陈直身上,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。他在庞大的工厂里,占有一席之地,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,不停地干着。每个月赚四五千元,勉强够吃饭。有一段时间,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,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,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。没有凳子,一站就是一整天。也没有窗户,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。玩手机是不可能的,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,只有人可以进去。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,那就是重复和空洞。
车间里的生活严格、精确、一丝不苟,机器从不休息,人也无法休息。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,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,因为“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”。
根据一份调查报告,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.85亿人。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,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。他们置身于城市,但却自成一体。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,有什么Ambition,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。
直到陈直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,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,如何在狭窄的出租房里思考哲学。
2011年,他在北京打工,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里。那里没有窗户,很潮湿,也很昏暗,他一个人住,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。看书的时候,他拿床当椅子。屋里没厕所,他得去外头上公厕。环境太差了,但也没什么办法。他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,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,就是在那期间,他配合英译本,读了一次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
这些年,他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,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还有北京,每去一个城市,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。他常说,哲学是他的“激情”与“使命”。他去北京打工,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。他去深圳富士康打工,下了班之后,要去富士康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。
他显得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格格不入,家里人觉得他不老实打工,妄想看什么哲学书。他开始变得焦虑,但是毫无办法,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。朋友这个词,他不敢轻易使用。因为以前在村里,他是最会读书的人,现在却成为最落魄的人。他把自己评价为一个“无用场的人”。
他从未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工。他经常会因为身份受到歧视。早年去店里买衣服,店员不招待他,甚至去理发,店员也不会搭理他。
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,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,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。但现在不太想了,因为都习惯了。他读叔本华的书,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。但他不觉得无聊,相反,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。
以下是他的自述:
车间里
翻译完理查德·波尔特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时,我正在厦门的工厂里打工。
我是个农民工,从2010年就开始打工。我只干短期工,长期的话,干不下去,做过最长的工作可能就半年左右。上一份工作做了三个多月就走了,和其他工作相比算是干得久的。我住在厦门集美区,这边有很多工厂和职业介绍所,一般都是中介介绍,进行劳务派遣。短期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高,时薪有20多块,但正式工的话底薪是很低的,厦门市最低工资那种。有人一个月可以挣六千,但需要一个月做300个工时,平均每天得做十一二个小时。
工厂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中国台湾公司,是苹果、小米这些手机厂的供应商。这里很多名称都用的中国台湾叫法,比如他们会把软件翻译成软体,这总让我想到软体动物,我还挺抗拒这些词的。
厂里有不同的生产线,有点胶机,还有组装摄像头的组立机。我就是维修组立机的。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,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,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。机器设置了各种防止受伤的机制,比如红外线那样的,好像叫做光栅。如果你的手阻碍了红外线,机器就会停止。
修机器和修车差不多,只是机器更小,立在地上,不需要升起来,所以我最多蹲下去。也不能移动,不然精度会受影响。机器也不是经常坏,坏了的话,有专门的人会叫我去修。每天站在那儿,待着的时间会比修的时间要多。车间里是恒温的,永远二十五六度。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,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。
这里没有窗户,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。公司电脑可以访问公司网站,电脑很烂的,我不会用它上网,屏幕会看瞎眼,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看那个显示屏。也没有凳子坐,就站一整天。玩手机是不可能,手机不可能带进去的。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,只有人可以进去。
我在岗上还要穿蓝色的无尘服,摄像头不能有灰尘或者颗粒,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。工种不同,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。我们是最底层的人,上面的经理、组长、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,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,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。
每天在车间里也没有想什么,需要修机器的话就修机器,有人跟我说话,我就说话,没人说话就在那儿发呆,但是不可能想什么海德格尔,那里面噪音太大了,很乏味的。
其他修机器的工友全都是男的,他们一般聊女人和游戏,我就默默听着,不主动得罪他们,但是也不插话。但他们聊嫖娼的时候,我就会走开。
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,好像没有任何意义。前几年,我会写点英文日记,天天都是upset、desperate 、dismayed这些词。今年开始,我对自己格外失望。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,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。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,海德格尔说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,就是存在问题,“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?”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希望能在思考的基础上写一点东西出来,实现自己的一些Ambition,所以开始尝试翻译。
其实翻译也没想象中那么难。大概十年前,我读一些中译版的哲学书感到很吃力,因为哲学术语,翻译成另一种语言,往往会变得生硬,那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原版的书,所以开始学英语。我用有道词典背单词,直接从最难的等级,GRE、托福开始背。学了两年,就能看英文原著了。翻译时,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字典,也没什么难的,真正难的是没有时间。
比如在这个工厂,休息是要请假的,如果不请假,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。很多人为了赚更多加班费,选择一天都不休息。因为我要翻译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一般都会每星期请一天假,也请不了更多假,一周请两天是批不下来的。请假意味着扣除双倍工资的加班费,一天扣两三百块。我们底薪只有1800块钱,也就是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,那些一天都不请假的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,8小时外的时间都算加班。
我的请假理由就是有事或者生病,不会说我要做翻译。整个工厂没有人知道我读哲学,也在翻译哲学书这个事情。我都是自己一个人,不会说这些的,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在搞什么。
下班后,我回家做的事都有优先级排序。最重要的是读书,我最近在读John Richardson(一位美国海德格尔学者)的《海德格尔》原著。读不进去的话我就做翻译,比如《寻求本真性: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》。如果翻译也不想干,什么都不想干了,我就看看豆瓣和知乎,微博我是不上的。前两年我注销删除了微博,那上面的信息太浅薄了。豆瓣的话,我感觉那边的人,可能稍微不那么平庸吧。
中间我还去过深圳富士康打工,从5月干到7月底,负责组装iPad的屏幕。首先需要测试一下,从检测机器上看屏幕的亮度均不均匀,有没有亮点,如果是不良品就会被处理掉。那儿的工作需要每天坐着,比做手机摄像头更累。机器会算好时间,最快速度大概一个人每天要装800个屏幕,30秒就得贴一个屏幕。那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,因为是流水线,你要干得很快,一旦分神的话,你就干不好。速度慢了被线长发现,就会挨骂。在那里,空虚倒是小事,就是太累了,特别是上夜班,更难。眼睛迷糊了,就去洗个冷水脸,或者站起来继续干。
在富士康打工的日子里,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中介为我们这些临时工租房,一个月三四百块钱,包水电,十个人住一间宿舍。屋子里紧凑放五张高低床,再加一个小独卫,此外连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都没有了。中介不让用大功率电器,所以连电水壶都用不了,在那里只能给手机充个电。深圳的夏天很热,幸好空调是24小时都开着的,因为舍友是随机分配,来自不同部门和车间,有人上夜班,有人上白班,作息全不一样。这样一来,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。
下了班,我拿着kindle随便找个地方看书,路边花坛都行,反正不会在宿舍看,因为我对人群比较敏感。富士康北门一出来就是清湖劳务工图书室,一些附近打工的人会在那里看书,我也爱去那看。
翻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空。每周休一天,我就去龙华文化艺术中心翻译书。那会我翻译比较急迫,会从早上9点翻到晚上8点,直到闭馆,一天大概能翻译三千个单词。但既要翻译又要看书的时候,进度会慢点,只能翻一千个单词。所以两百页左右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翻译完。
我觉得底层社会好像感觉差不多都这样累。这种感受我无法描述,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,或许别的人能够真切地描述这种感受,但是我缺乏这种真切描述的能力。一直都是这样,你也知道,哲学都是那些很晦涩的抽象概念的,所以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。
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,我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。但现在我就不太想这些了,因为都习惯了。想了,也没什么办法,是吧?
不合时宜的人
我也读过一点大学,但是没读完就退学了。
那是2008年,一个所谓的二本。专业是数学。但我当时想要寻找最本质的东西。比如从数学上来讲,我想知道自然数的本质是什么。还会想我们意识的本质是什么,还有视觉的本质,我很好奇这些。所以后来觉得上大学的课,比如数学分析,常微分、解析几何这样子,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我只能自己看书,自己去思考,那会主要看康德、黑格尔,能带给我很多对现象的理解,甚至是对本质的理解。特别是黑格尔的那个哲学,他所谓的绝对精神,是描述整个人类历史,整个世界,整个宇宙。
黑格尔说,理性是宇宙的法则,他就说这么一句话,我感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但这只是那个时候的看法,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的。
到最后,我过于沉迷哲学,考试也不参加了。我完全遗忘了我的专业。大二开始,所有的课我都不上。学分制什么的太复杂,我也不太懂,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书。学校方面叫我主动退学,我一下就同意了。我去找辅导员签字的时候,才第一次和他说话。
现实中,我可能会有社会交际的压力。小时候,我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,往往这样的人都比较软弱、懦弱、谨慎。所以一般不会主动说话。我不希望会provoke(刺激)到别人,也不想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,即便不一样,我也不会说出来的。所以大学时我很边缘,住四人宿舍,只有一个室友会主动和我说话,他们和其他人一样,爱聊女人。我也没参加社团,但我觉得并不孤独,读哲学书,能让我暂时地忘掉现实的东西。也说不上是逃避,这个不是我读哲学的原因。我读哲学主要是问题导向,我有一些希望解决的问题。绝对不是要逃避什么,不是这样的。
那时候想法很简单,我觉得退学比上学好,学校压根没有哲学系,我退学了反而可以回家自学。我从没想过未来和工作怎么办,对这些我是无所谓的。但没想到,家里人听说我退学,不让我回去。我在江西的农村长大,在他们的概念里,不读书,就只能去打工。哲学是什么,跟他们解释不通,于是我就只能去打工了。
我的第一份工,是在浙江一个乡镇服装厂踩缝纫机,当时被中介从杭州骗到了诸暨,干了一个月,工资都没多少,就500块钱。缝纫机对我来说很难,需要不停踩踏板,有一次做羽绒服,我没有搞好,把里面的羽绒都弄出来,就被骂了。我感觉干不来,和我一起去的,有些人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学会,但我学不会。
第二份工,我去了制作方便面桶的一个工厂,也是通过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找到的,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们就是人力资源吧。那份工作也是机器在做,我就用机器卷一下那种纸呗,卷一下就搞定了。很机械,但是也比较累。有一次,我在线上的时候,接了一个电话,就被辞退了,就是这样严格。那时厂里不缺人,随时都可以招到人,只要你不听他的话,他就叫你滚蛋。
我做过最累的一份活儿,是2018年在无锡搬货。干了两个多月,每天干12个小时,从上午11干到晚上11点,什么货都有,大瓶水、饮料、还有大米,因为超市订单比较多,有班长盯着我们,所以中间不准休息,一天下来真的很累很累,是说不出来的累。
打工这些年住宿舍,室友之间从来不会说话的,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,因为工作太累,人来来去去,离职率很高。这十一年,可能就两个工友会关系近一点,但是我换了几次手机号,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了。
那两个人是我曾经的朋友。七八年前,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,就向他一个人借了100块,我以为借不到,没想到他借给我了,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另外一个跟我说话比较多,一些琐碎的事情比较聊得来,我是从不和任何人聊哲学的。
我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,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还有北京,每去一个城市我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。2011年,我从南方大老远跑去北京打工,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,我想去那里多读点书。我花四百块,在通州租了间六七平米的地下室。地下室没有窗户,很潮湿,也很昏暗,我一个人住,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,看书的时候拿床当椅子。屋里没厕所,还得去外头上公厕。环境太差了,但也没什么办法。
从通州到国图比较远,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,所以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,更多的时候就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,看多了,现在眼睛视力都不好。
哲学是我的passion
哲学是我的passion,是commitment。用汉语的话,就是“激情”与“使命感”。可能“使命感”过于强烈,那么commitment译为“承诺、许诺”也可以,但是“承诺、许诺”又太弱了。我在豆瓣小组上发过一个帖子——《使命作为人生的意义》。当我感到无意义的时候,就去找那些如玄奘、张益唐、陈景润这样的人来激励自己,因为就像北大数学天才张益唐,也有一段时间是不读数学的。这能帮助我走出无意义感。
大多数时候,我对哲学的痴迷会让我对外界的恶意置之度外,但生活还是时刻提醒我认清自己作为“农民工”的社会身份。
可以说,童年对我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。我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人,有拳脚交加的暴力,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。父亲总是这样对我,只要他心情不好,洗个澡,看个电视,他都会骂你。他个子并不高大,但只要阴沉着脸,我就对他本能感到害怕。直到二十多岁,他骂我,我才敢回骂。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,那就是没有感情,我们基本上已经断绝了关系。
我常想,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,现在肯定不一样。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,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。说实在的,我现在也很压抑,比如赚不到钱,读不懂哲学,交不到朋友。我越来越内向,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。
前几年,我尝试过改变自己所谓内向的性格,也想成为那种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。但很难,我从来不和人聊哲学,这在农民工里太另类了,别人可能会嘲笑我,所以我更愿意把它隐藏起来。后来还是觉得就继续维持现状吧,改不了的。
但我不孤独,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。压抑是生活的常态,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。
我之前会读叔本华的书,他说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,他的这种“悲观主义”可能在哲学上意义不大。我不觉得无聊——至少在大部分时候,相反,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,在车间的生活只是一些插曲,这些东西不值一提。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。
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间隙,萨特、克尔凯郭尔、胡塞尔、德勒兹,还有人类学的列维·施特劳斯,这些我都会读。直到2017年,我在哲学上体会到了最深最无力的绝望。当时,我很想写几篇哲学论文发表,标题都拟好了,但是写不出来。
写论文需要查很多资料和二手文献,我感觉我没有这种能力。第一,我没这么多书,第二,这些东西也不大好找。而且那时候我哲学水平比较低,还在打工,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。
最多的一篇写了几百字,看着空空的电脑屏幕,我根本写不下去。自学这么多年后才发现,我可能搞不了哲学,太有挫败感了。那会我在汕头的五金厂打工,2017年4月1日,我在日记里写:我彻底不干了。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,以后如果有机会,我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。哲学本身我干不了,必须放弃!
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,因为听我妈说,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挣了好几百万,而我甚至连几千元都没攒到。我妈看我不老实打工,还妄想看什么哲学书,就会用这种例子来刺激我。因为我不会赚钱,她也连带着被邻居看不起、嘲笑,甚至侮辱。
在社会上,我因为农民工的身份,受过不少歧视。早年去店里买衣服,店员不招待我,甚至去理发,店员也不会搭理我。
我的所有微信好友都是18岁以前认识的人,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识过新的人。朋友这个词,我不敢轻易使用。像我这样子,第一赚不到钱,没房没车。第二老大不小才结婚,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娶不到老婆的。
2021年5月,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自述,“从最会读书的人变为最落魄的人……”小学与初中,我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名或前几名,还被老师派去参加县城数学竞赛,中考的时候,我考了全校第一名,在农村算是“最会读书的人”。但现在,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做各种生意,搞建筑啊、盖房子啊,或者开个店铺,我在所有人之中是最不会赚钱的。
去年下半年,一个过去的朋友突然来广东找我,他在外面开店,我们就聊了会天。当时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,大概我是“混”的最差的,大家都瞧不起我。
说完这句话,我等待着他的回应,但他什么也没说。他默认了。
我想大多数“凡人”是很乐意看到我这样的。这也是人之常情,看到别人落魄,过的不好,自己也就获得了满足。《陆犯焉识》里,陆焉识被他姨娘说是“无用场的人”,我也觉得自己是无用场的人,就像废物一样。
我被哲学伤透了心,很长一段时间,我不碰它了。
人生道路的三阶段
我学哲学没有任何所谓的现实目的,绝对没有,如果有的话,那是一种悲哀。但我不觉得哲学是无用的。哲学能够改变人的存在,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。不是一般的改变,而是根本的改变。
我最早进车间的时候,常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。第一阶段是那审美的,就是依靠感官来生活,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,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。克尔凯郭尔说这种人本质上是最绝望的,虽然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很绝望。我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这样。他们谈女人,嫖娼,生活无非是围绕这些生物本能展开的。
第二阶段是那伦理的,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,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。第三阶段是那宗教的,只有超越社会道德观念或伦理观念,超越普遍性的人,才能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一度希望自己能超越世俗社会,成为所谓的single individual (孤独个体),但尽管不情愿,我依旧接受了结婚、生子,成为一个处于第二阶段的普通人。
妻子来自同一个县城,小我3岁,我们2020年初相亲认识,很快就结婚了。2月领证时疫情很严重,直到去年年底才补办婚礼。农村婚礼很朴素,没有请伴郎伴娘,也没有闹洞房,在院子里摆了一二十桌酒席,杀只鸡,去祠堂拜祖宗,婚就结完了。
婚礼的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,好像是12月的某一天吧。毕竟不是我自己操办的,日子不记得也正常。没过多久儿子出生,妻子是剖腹产,我和我妈一直陪着她。看到孩子出生,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,这样说也许很无情,但他具体哪天出生的,我确实记不太清了。
妻子上的中专。她的工资比我高,因为她加班比较多。周末都不请假的,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,我叫她休息,她都不愿意。就为了多挣两三百块钱加班费。她在工厂穿红色的无尘服,检查那个镜头啊,摄像机有没有污点什么的。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起去,在不同的车间上班,然后晚上在一起回来。她现在上夜班,从晚上八点半开始,白天的时候她在睡觉,早上回到这里可能九点了。
平时我会和妻子说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,在她面前我能更坦率、更真实地表达自己。只不过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,我都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平时除了日常琐碎的事情,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
我妻子其实也理解不了我的想法,她绝对理解不了哲学,理解不了海德格尔。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讲过,但她不感兴趣,就叫我不要说。她下了班就喜欢玩手机,戴耳机看抖音,我看书,彼此互不打扰。
今年以来,由失望而滋生的无意义感,指引我再次拾起了海德格尔。我翻译完了理查德·波尔特的《海德格尔导论》,想要找个出版社出版。我在豆瓣上私信了一些出版社,问编辑能不能出版,他们都没有回复我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,这样的学术性书是很难出版的,因为卖不出去啊。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,我感到很无力。
我向往着能够再进入大学读书。虽然以前退过学,但那时候,我没想到在这个社会上,尤其在底层社会是这样的。无论是学数学还是学哲学,最后还是得面临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。现在通过打工,一个月赚四五千,只能维持我吃饭。
最近我从那个工厂离职了,一时也找不到工作,就去厦门图书馆读书,从开馆待到晚上八点闭馆。但是最终我还是得去打工。在流水线上,一个一个地干。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,12个小时,中午吃饭一小时。每隔一个月就是夜班。不停地干,是不会让那个机器休息的,人也永远不会休息。
陈直为化名。头图来源于视觉中国。
来源:谷雨实验室
图片翻摄自网路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
 點評
點評 微信
微信 微博
微博